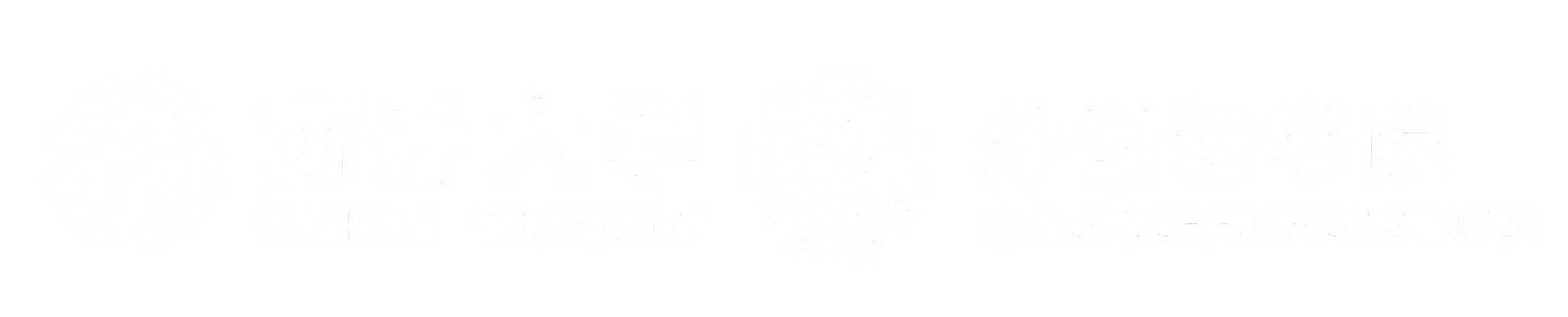9月26日,73岁的美国老人罗兰·费希尔再次来到中国,女儿、女婿跟着他来了;老伴儿蕾切尔体弱多病,很少再出家门,但这回她带着满箱的药品,也跟着一起来了,只因此行非同寻常,天津市人民政府将2009年度的“海河友谊奖”颁给了费希尔。
荣获“海河友谊奖”,费希尔心情激动,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惊诧得难以置信,因为他早已离开了中国,在他看来那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往事了,没想到中国人民仍未忘记他,天津政府还要颁奖给他,可见中国人是多么地看重友情。
费希尔,一位特殊的美国朋友,早在少年时代,他就迷上了中国;自1982年起,他更是与中国、特别是天津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把一名教师人生中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中国;他以奇特的教学方式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他帮助好多中国学生实现了留学的梦想;他把自己在美国的家办成了中国交流学者和留学生的“接待站”。当初他来中国教学,是出自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和对贫困中国的同情,不想最后他却把自己变成了半个中国人,以致他落叶归根后仍然整天思念着中国、天津,终日浸沉在他所迷恋的中华文化里。“海河友谊奖”让费希尔成为新闻人物,记者更感兴趣的,则是这位美国老人奇特的世界观,以及他那不乏传奇色彩的人生。
(一)迷恋中国
1982年6月1日、费希尔46岁生日那天,他和妻子蕾切尔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那是他们第一次来到中国,要去天津的南开大学外文系教书。
费希尔走下舷梯,一个罕见的场面把他惊得目瞪口呆——飞机跑道上竟然出现一辆驴车,载着草料慢悠悠走过。“天哪!这是中国?”他想。
汽车把费希尔夫妇拉进北京城,城里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到处是自行车群的铃铛声;友谊宾馆当年可是北京最好的涉外饭店,他们看到的却是嘎吱作响的地板和中央凹陷下去的床。中国朋友以最好的条件招待他们,可惜一切都与他们昨日的生活相差太远。
费希尔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中部一个名叫亚历山大的小镇,那里到处是清澈的湖泊。读到高中时,他最好的一个朋友让他偶然地知道了中国。他朋友的祖父曾经工作、生活在中国,退休后那老人仍旧深切地迷恋中国,便离开人群,在一个湖边上建起一座中式的宅院,装饰出一个完全中式的家,中国的书画、雕塑、书籍和家具等,形形色色的中国古董布满所有房屋,到处弥漫着檀香和樟脑的气息。一天,那好朋友对费希尔说“带你去个奇异的地方”,便把他领到那湖边。一进那宅院,费希尔顿时被他从未见过的东方文明所吸引。朋友的奶奶给他们一段段地讲述在中国的经历,说那是一个拥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国度,更引起了费希尔对中国的兴趣。从那起,费希尔经常要求那位朋友带他去看望两位老人,让他们给他讲中国的故事,教他如何用筷子夹食花生、米粒和葡萄干。从那儿起,费希尔开始对中国的文化着迷。
不久,费希尔弄到第一本英文版中国小说《骆驼祥子》,透过这本书,他了解到一点中国的风土民情。随后,凡与中国有关的材料,费希尔找到了都会认真阅读和收藏,听说哪儿要播放有关中国的电影,他一定去看。当时中、美是敌对的两大阵营,费希尔看到的资料和电影,美言中国的内容几乎没有,却不知为什么打不掉费希尔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相反,他想去中国看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1974年,费希尔和夫人蕾切尔在新西兰教书。那时新西兰已和中国建有一定外交关系,费希尔从新西兰政府那儿千方百计弄到两张新西兰教育工作者走访中国的许可,想以新西兰教师的身份走访中国,可惜他们的美国护照绊住了他们,费希尔非常遗憾。
1979年费希尔夫妇重回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教书,这时尽管中美已有外交关系,但是想要走访中国还是困难重重。是年10月,费希尔听朋友说明尼苏达大学来了4位中国南开大学的访问学者,他立刻让朋友介绍他认识这些中国人,他把他们请到家里作客;拉他们去密西西比河源头区野营,一次次地交流,为的是从中国朋友嘴里得到有关中国的真实资料。后来,明尼苏达大学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越来越多,其中好多学者都成了费希尔家的座上客。
随着对中国认识的加深,费希尔夫妇越加向往中国。1981年,他们决定调整自己的人生计划,变移民新西兰为旅居中国,到那神秘的文明古国里生活体验上一个时期。费希尔费尽周折,终于在1982年得到了天津南开大学的邀请。
费希尔夫妇被请来外文系教授英语。校方提供给他们一套最好的住房,但与他们在美国的住房相比,那房子逼仄得不可思议。加之供应短缺,食堂一连十几天总是炒白菜,自己开伙,蛋肉油糖的消费又都有限制。然而,尽管如此,却扑灭不了费希尔夫妇的激情,相反他们喜欢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发现:这里的人民纯朴、热情;这里的学生求知欲特强,过去他们从未见过学习如此刻苦的孩子。而且,费希尔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约翰·菲利普斯当时碰巧也在南开大学教书,菲利普斯告诉费希尔说,这里的人民注重友情,这个国家很有希望,这儿的文化博大精深。随后,费希尔夫妇在中国一呆就是5年,直至蕾切尔生病,不得不回国治疗。
(二)杰出的使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大专院校急需英语教学人才,费希尔夫妇的到来堪称雪中送炭。
费希尔夫妇一到,南开大学就把33名申请加拿大留学亟需通过托福考试的学生交给他们。蕾切尔擅长教授英语写作,她的课学生们特别爱听。费希尔更棒,他拿过艺术和戏剧两个硕士学位,他把自己的特长糅在英语教学中。他带来很多原版美国影片,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和《海伦凯勒》等,课堂上他一边播放影片,一边讲授英文生活用语,让学生模仿、练习,提高听力和口语的能力。他的课生动、活泼,他的语言和表情带有戏剧的夸张,而且幽默。每逢费希尔讲课,教室里走道上都挤满站客,学生们喜欢这个留着络腮胡子、长得像列宁的外籍老师。半年后,这批学生31人通过了托福的测试。
转年暑假,费希尔夫妇回国探亲,他们自己的儿子读美国大学一年级还没人照顾呢。假期结束重返中国时,费希尔带来更多、将近60部原版美国影片,以致引起中国海关的注意,过关时全被扣住。后来,中国海关了解了这位美国教师的动机,将影片全部退还给他,费希尔的课堂依旧堂堂爆满。
利用影片寓教于乐,引学生进入原态的语境,费希尔式的教学法,对当时中国的外语教学,是一种创新,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改革。后来,费希尔又用排演英语话剧的方法,提高学生掌握、运用英语的能力。他排的第一个剧目是美国音乐剧《俄克拉荷马》。上课就是演戏,演戏就算上课,外文系师生群情高涨,争演其中的角色。为让更多的人参与其间,费希尔扩大合唱团的规模。同时为了省钱,他还操起锤子、电锯,叮叮当当地制作道具。最后,南开版美国音乐剧《俄克拉荷马》连演5场,场场博得满堂彩,在津的外国人,几乎都来欣赏了这部由中国学生表演的美国戏。
后来,费希尔得知南开大学早就拥有排演话剧的传统,他萌发一个念头:何不让学生们排演一部中国话剧,如《雷雨》,拿到美国去演出,既锻炼学生运用英文的水平,让学生们去接触一下英语国家,又能让美国民众欣赏到中国的文化。费希尔去北京拜访曹禺,请求曹先生支持他的主张。征得曹禺的同意后,费希尔开始不遗余力地排演他的英语版话剧《雷雨》。最后,这部话剧在天津演出大获成功,但所有的人,除费希尔之外,对这部戏能否走进美国表示怀疑,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让一个并非专业、皆由青年学生组成的团队出访美国,谈何容易?
费希尔具有从不轻言放弃的性格,对既定目标,剩百分之一的希望,他也要百分之百地去努力。《雷雨》剧组演员十余名,美国驻华大使馆签证处那里,费希尔得挨个儿担保他们没有移民的倾向,费希尔就一普通美国公民,没任何政治背景,他就靠他的执著和真诚,一家家地联系能够邀请《雷雨》剧组前去演出的美国院校,一趟趟地游说美国驻华使馆签证官,最终办成了这件事。
1986年1月,费希尔改编、由其中国学生主演的中国经典话剧《雷雨》,用英语在美国明尼苏达、圣克劳德等十余所大学巡演,先后11场,场场爆满,大获成功。美国29家英文报刊报道《雷雨》进入美国的消息,斯坦福时报评论说:“中国《雷雨》‘袭击’了斯特灵大厅(斯坦福大学礼堂)。”
当时中美文化交流很少,中国人渴望了解科技发达的美国社会,美国民众同样也想了解神秘的中国。他把美国戏剧电影通过教学传给中国学生,又把中国的《雷雨》巧妙地引进到美国。后来,他再接再厉,又改编、排演了第二部话剧《洋车夫》,也就是中国的《骆驼祥子》。1987年费希尔的剧组再次出访美国。这回他居然把工作做到美国西北航空公司总部,他力陈中美文化交流的意义,竟让这家航空公司为剧组提供了免费的机票,从而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洋车夫》在美国十大院校巡演,盛况空前。
费希尔奇特的教学方式,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也提高了学生的文化素质。而通过教学,费希尔也与他的学生、同事,乃至这个国家迅速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以致改变了他原先只在中国呆上两年的计划。
费希尔在华期间,帮助很多学生解决了留学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特别需要派出大批留学生去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知识和理念。但那时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很难,且不说赴美签证一关如何严格,那时绝大多数学生出国留学的前提,是必须拥有对方院校提供的奖学金。费希尔知道留学对一个学生的命运来说意味着什么,更知道培养大量优秀人才对渴望崛起的中国具有的意义,因此他掏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帮助他的学生们解决赴美留学的难题,从联系美国的学校、争取奖学金,一直到为每一个学生提供担保、办理签证。话剧《雷雨》中饰演繁漪的蔡本红去了美国圣克劳德大学,其全额奖学金,是费希尔亲自去找校长麦克唐纳给谈下来的;饰演大少爷的刘思远想去美国留学,美国驻华大使馆那儿一次次地拒签,刘思远本人都已心灰意冷,费希尔一次次地去找美国大使馆,写信、面谈,最终帮他拿到了签证。后来,连一些不是费希尔学生的人,也来求助费希尔。20多年来,不知有多少中国学生和青年学者,在费希尔的帮助下实现了留学或访问美国的梦想,其中很多人学成归来后已成某一行业的栋梁,在《洋车夫》中演祥子的谢哲强,如今是美国某大公司驻中国的首席代表;在《雷雨》中演周朴园的孙学军,现是英国某投资公司东亚部主任……费希尔夫妇南开校园执教5年,为中国培养英语人才,为中国外语教学创新,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三)不尽的思念
1987年,蕾切尔生病需要回国治疗,费希尔舍不得离开老伴儿,不得不随她一起离开中国。临走时,费希尔穿的T恤衫上印有一行大字:“我情愿留在天津”。他的包里还藏有一件,写的是“终身难忘”。可见其对中国、对天津恋恋不舍的心情。
回国后,费希尔也像他高中时见过的、那对从中国回去的老人那样,在自己家里摆满了中国的家具、木刻、铜雕、泥塑、书法、绘画和瓷器等各式各样的古董和艺术品。那些东西都是他过去在天津沈阳道、北京潘家园淘来的,搬家时全都当作宝贝似的一件不落地运到美国。他终日沉浸在那些宝贝给他营造的氛围里,借以重温他曾在中国的日子。他甚至把他的中国名“费念华”刻成木牌挂在房门上;将其花园命名为“秋实园”;把他养的一对中国狮子狗叫做“包子”和“饺子”,因为中餐里这是他最爱的两样东西,后来想想不对,怎能把爱犬比作食品?遂又改称“和平”和“友谊”。在中国的那些岁月里,生活贫困,但他快乐无比,一是他觉得他自己对别人来说是一个特别有用的人,他的工作能让很多人改变自己的境况,甚至是人生;二是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中国的戏剧文化,哪怕是他难以听懂的相声和快板书,都能让酷爱戏剧艺术的他感到陶醉;再就是他和许多中国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回国后,费希尔选择了在圣克劳德大学国际交流处里的一份工作,专门负责该校与中国、特别是南开大学的交流。履职期间,费希尔积极促进圣克劳德州立大学与南开大学的交流,他创造出各种机会,让他的美国同事了解和学习中国,同时也让更多的中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国读书。圣克劳德大学派出教师赴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去外文系任教;南开大学历任校长和许多学者都曾去圣克劳德州立大学访问或讲学。就因中国的情结,费希尔甘作中美院校间学术交流的桥梁。
2002年,费希尔退休,回家专职照顾老伴儿。老伴儿有病,行走不便,费希尔愣自己动手,在居室里挖坑、拆房顶,为老伴儿装了一部简易的电梯。费希尔以为自己从此就会渐渐地与世隔离了,不想中国的朋友们从未忘记他,更未因其退休而疏远他,凡去明尼苏达的人,都去看望他。
2004年,费希尔的老朋友、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蒋华上教授去家里拜访费希尔,谈起天津经济正在飞速发展,南开大学为配合滨海新区的建设,特别建立了滨海学院,蒋教授希望费希尔先生继续帮助一下老朋友,为这所新兴的大学做些工作,费希尔听后欣然应允。
2005年10月,费希尔带着一个“教授团”访问南开大学滨海学院。“教授团”13人,全是美国退休的老教授,其中有的曾是校长、副校长、或是系主任。这些老教授经费希尔动员,自费来天津滨海学院,开展为期3周的“中美友好文化交流月”的活动。老教授们各自为战,授课,组织英语角,举办英语演讲,帮助学生排演英语话剧,开办“美国文化系列讲座”。一连20多天,老教授们在滨海学院掀起英语教学的热潮,校园里到处是一群群的中国学生围着美国教授热聊、求教的盛况,学生们通过老教授们的讲座加深了对美国的了解;老教授们通过这次访问,加深了对中国人文和社会的认识。
“教授团”里,一位老教授曾对中国抱有很深的成见,他的哥哥当年当兵曾在朝鲜战场上负伤,战争的记忆始终藏在他心底,起初这位老教授不想参加这项活动,费希尔一听反倒非要动员他亲自来体验一下中国。结果,短短十几天,那位教授就跟费希尔说:“没想到中国学生这么好学;没想到中国人这么友好,这么热爱和平,此行改变了我对中国的印象。”费希尔听了非常高兴,把这事儿当作一项成就告诉他的朋友蒋华上。费希尔就是这样,在美国他听不得有人说中国的不是。
回国后,费希尔又在圣克劳德州立大学和南开大学滨海学院之间搭建起一座交流的平台,促使两校正式签署了合作的协议,而且他还担当起滨海学院国际学术交流的顾问。从此,费希尔重新忙碌起来,2008年,滨海学院十几名学生赴圣克劳德州立大学,开展为期3周的英语培训和文化交流活动;滨海学院外语系3名毕业生,拿着圣克劳德州立大学全额奖学金赴美攻读硕士学位;今年,滨海学院学生民乐团赴美巡回演出,都是费希尔从中努力促成的结果。
如今,一提费希尔,他的那些中国朋友言语中无不对他充满感激之情。因为,这位美国老人对待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美国人待客一般是不把朋友带到家里的。费希尔不然,经他联系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圣克劳德大学留学或访问的学生和学者,即使素不相识,只要一到美国,他都要驱车上百公里到机场去接站。见面费希尔先给对方一个热情的拥抱,然后把客人接到家里热情款待,白吃白住,费用免提。有时一次去的人太多,费希尔腾出所有房间也睡不开,他就在客厅里面打地铺;有时十几个中国学生都去吃饭,费希尔家就成了食堂。问题是费希尔夫妇并不富裕,在美国他们就是一对普通的教师,靠拿退休金生活,但一沾中国朋友,特别是中国学生,他们毫不吝啬。
2005年费希尔率“教授团”访问南开大学滨海学院时,发现教授们捐献给学院的外文书籍特受欢迎,回国后他就在大学里、在网上动员人们为中国的学生捐书。人家谁要捐书,打电话给他,他开车把那些书籍一点点地拉到家里,攒多了,动手打只大木箱,把书一捆捆包好装里面,然后借铲车把大木箱铲到借来的卡车上,他开着卡车把书送到机场,运往中国南开大学滨海学院。4年,费希尔发给滨海学院的赠书多达5843册,足够开办一间阅览室。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得的是27年不断地做着那好事;一个人的能力有高低,难得的是他能全力以赴地奉献自己的力量,鉴于罗兰·费希尔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特别是在初期中国最困难的阶段,为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中美民间文化交流坚持不懈地做出贡献,天津市人民政府今年授予他“海河友谊奖”。
(四)中国人民永远的朋友
一晃27年,费希尔出入中国数十次,唯有今年9月这次让他特别兴奋和激动。70多岁的人了,在西方人情淡薄的社会里已属被人遗忘的阶层,不想遥远的中国仍在牢记着他的友情、他的功绩,为此他非常感动。
9月27日,费希尔出席了中国国家外专局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外国友好人士联谊会,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9月28日,费希尔出席天津市政府举办的中外友好人士国庆招待会,受到市领导的接见。
9月29日,滨海学院的朋友们请他乘船夜游海河。灯光下海河两岸美轮美奂,看得费希尔感慨万千。他对朋友们说:“想不到天津能建设得这么美。我现在的感觉,竟像是一个乡巴佬突然来到了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此刻,费希尔想起他初到中国时看到的那辆穿越飞机跑道的驴车;想到了购买各种食物时所要出具的票证,他曾同情这个国家的贫困,决心为这个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今他看到这个国家令人惊奇地壮大起来,他感到自豪的是,他自46岁起做了一个重大的选择,就是他把自己后半生所从事的事业与这个国家的发展联系了起来,实践证明他的选择没错,他的期望没有落空。
10月1日上午,费希尔宣布哪儿也不去,就在宾馆的房间里观看中国国庆大阅兵。那场大阅兵,看得费希尔像一个中国人那样激动。他打电话给他的朋友蒋华上教授说:“请你一定要给我买到这阅兵的光盘。我要把它带回美国,我要放给我所有的朋友看!”
《天津日报》2009.11.27